「我有幸第一次看到生長中的神經元軸突有個奇妙的末梢結構。在我自己製備的雞胚胎脊髓切片中,這個末梢看起來就像個充滿原生質的錐體,進行著變形蟲式的移動。可將它比擬作一個活的攻城錘,柔軟而靈活,它前進,便可機械性地推開擋在它的路徑上的阻礙,直到抵達在它外圍的終點。這個奇特的端點錐節,我要將它命名為『生長錐』。」–Santiago Ramon y Cajal, 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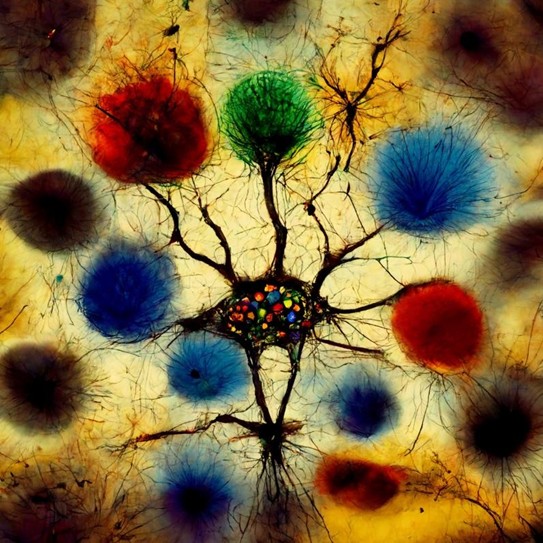
▲利用AI平台Midjournal繪製的神經元
神經科學之父 Ramon y Cajal利用一般光學顯微鏡,將固定後的神經組織樣本利用高爾基染色法染色,距今百年前,首次描述到軸突與樹突尖端的特殊結構並將其稱為「生長錐」(Ramon y Cajal, 1890, 1911, 1929)。Cajal的藝術天賦,將顯微鏡下所看到的神經系統轉化為非常精確的圖畫,清楚地畫出腦組織內層層疊疊神經連結的架構。且他僅從靜態圖像就能推敲出次細胞結構一系列的動態功能,是先知般的存在。隨後Ross Granville Harrison發明了能將組織細胞分離並在活體外培養的技術,成為首位觀測活的生長錐行為的科學家。Harrison觀察到生長錐在組織培養皿中持續移動,不斷局部延伸與收縮,正如同Cajal推測的那樣,這個奇妙的錐形端點的確是屬於正在往前生長中的軸突的一部分。除了對生長錐的描述之外,Cajal首先認定神經元就是中樞神經系統的最基本元件,還發現了突觸(synapse),也斷言神經元的型態與功能具有極性:神經系統的訊息傳遞應該是由細胞本體或樹突接收,由長軸突投遞出去。而這些預言成為神經細胞學家的研究素材,前仆後繼以更高階的儀器或更精確的實驗方法,想應證Cajal的理論。現今的神經細胞學家的確擁有Cajal時代聞所未聞的基因圖譜,分子克隆,生物化學反應,和超高解析度螢光影像等研究技術與知識,但我們目前仍然還追趕著Cajal對「攻城錐」(battering ram)的想像。儘管科學家們更喜歡在自然界中尋找簡單且反覆出現的主題,但生長錐非常複雜,所有的生長錐都不盡相同,並且在神經發育過程中有多種途徑可以相互協調生長錐的行為。就如同天上繁星運行的規則,Cajal為我們描繪了不同星系的樣貌,甚至預測出星體移動的軌跡,只是一百年後,科學家們是否推導出屬於神經科學的重力場公式了呢?簡短的答案是,還沒。但我們亦非全無進步,只是偶而迷失在神經細胞生長的多重宇宙。因此在這次的專文裡,讓我們試著解釋Cajal這最初的觀察:柔軟而靈活的生長錐,何以攻城?
在活體外均質的環境下,起初細胞看似無目的的漫步,給它一些誘因,它就會顯現出一些本性。R.G.Harrison系統性的利用兩棲類(如青蛙)的神經母細胞來研究細胞在不同介質上的行為,很快地他便發現,細胞總是緊貼著固態的表面攀爬。Harrison稱這樣的行為為「contact guidance」。比如說在混著蜘蛛絲的懸浮培養滴裡,神經母細胞只選擇黏附在蜘蛛絲上,並沿著細絲延展。隨後 Paul Alfred Weiss也注意到細胞總是沿著玻璃表面的刻痕生長。但細胞並非毫無選擇地黏著在環境周遭的任何固態表面,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細胞膜上的受體是否與固態表面產生交互作用而活化。活化後的受體引發細胞膜下的黏附蛋白體聚集,啟動連串的生化反應,促使細胞骨架產生變化,也改變了細胞膜的張力。接著已活化的受體便隨著細胞膜內吞反應進細胞內而失效,解除局部的反應。在細胞探索表面環境時,細胞膜上每個受體皆進行著這樣的循環,動態的維持著細胞對周圍環境的敏感性,時時偵測著在行進路徑上的各種變化,而非死黏於介質表面。
對生物體而言,最不消耗能量的移動策略就是最好的移動策略。細胞本體的移動機制也可用來解釋軸突的生長策略,藉由生長錐的移動能力將軸突精確的延伸到相當遠的遠端 (最遠相當是一個人行走1萬公里遠的距離)。科學家很快地發現不同腦區的軸突遠程投射鮮少出現失誤,總是在既定的活性可朔期開始之前,抵達正確的腦區或周邊組織,與下游細胞產生突觸連結。試想開車旅行若要達到這般的準確性,駕駛必定好好規劃了行程,油料充足,遵照路標指引,沒錯過任何交流道出口。因此完成正確的遠程神經網絡連結需要幾個前提:細胞本體適當控制基因表現,軸突主幹持續延展變長,生長錐上表現適當引導因子接受器,以及組織環境在路徑上已鋪好軸突引導因子。至於這四者間如何有效相互協調,至今依舊是個待解的重要問題。從90年代開始,科學家利用單株抗體或雞胚胎的部分腦組織萃取物等方式設計實驗進行篩選,發現了幾類經典的軸突引導分子,包括netrins,BDNF,semaphorins,ephrins與slits(名單緩慢持續增加中)。這些分子存在在細胞外間質中或直接由標的細胞釋放,藉由影響生長錐的行進速度與方向來吸引或排斥軸突的靠近。有些甚至可造成生長錐塌陷導致軸突轉換運動模式。在細胞膜上相對應的軸突引導受體也陸續被篩選出來。結合這些知識,科學家們便可利用基因突變模式動物或將引導分子塗在玻片上(體外條紋試驗法)來檢視軸突生長對這些分子的依賴性,結果在在驗證了Cajal的預言:生長錐確實具有「精細的化學敏感性」(Cajal,1911)。如此若能讓生長錐兩側的引導分子受體更迭的速度產生不對稱,便能使軸突的移動產生方向性。也由於生長錐的高敏感度,不論是化學性或物理性的因子皆可有可能影響軸突生長,包括機械性引導,電場,利用不同黏附性所引發不同的訊息傳遞路徑,或引導分子梯度等,都可成
為生長錐認識的交通號誌或路標。但也因為培養在活體外硬介質的生長錐與軟組織裡的生長錐,不必然利用相同的作用機制來主導軸突生長,這使得我們在解讀相關研究結果需要更加小心。
生長錐長在活體外培養盤上的形狀就像隻正在彈鋼琴的手,張開的手掌,用指尖以微小的力量但極快的速度交替彈奏。神經軸突向前移動、縮回,改變方向與再生皆需要藉由改變細胞骨架的動態來執行,神經細胞學家對引發此類事件的環境因素以及如何將這些連串的生化反應轉化為「機械力」施加在其生長環境上也非常感興趣。科學家們普遍認為,無論何種細胞訊息傳遞,最終必須至少對生長錐內的肌動蛋白(actin)或微管(microtubule)細胞骨架陣列產生部分改變。肌動蛋白絲和微管被配置成密集且高度有序的陣列,肌動蛋白絲高度集中在生長錐的前緣,是絲狀偽足 (filopodia)與片狀偽足(lamellipodia)的核心結構。不管是肌球蛋白(myosin)的收縮性或是肌動蛋白絲(F-actin)的組裝和拆卸動態都可參與改變生長錐形態和行為。微管也隨時處於同步進行組裝和拆卸的動態平衡狀態,沿著長軸突形成緻密的微管束,延伸到生長錐中以「遇到」緻密的肌動蛋白細胞骨架。事實上,研究這三種細胞骨架系統如何相互結合可能是理解生長錐如何移動前往遠方的關鍵。
若以細胞骨架蛋白的種類與架構來定義,生長錐可分為三個亞區:1)中央域(C-domain),位於或靠近軸突軸的末端,主要由微管束組成;2)外圍域(P-domain),分佈在生長錐最前緣的周圍,主要由肌動蛋白絲組成;3) 過渡區 (T-zone),代表C和P域之間的接口,聚集著微管-肌動蛋白交聯分子,例如非肌肉肌球蛋白II(non-muscle myosinII;NMII)和發育調節分子腦蛋白(drebrin)。這樣特別的架構非常類似於人類的手部結構:C-domain是前臂橈骨末梢,T-zone是腕骨與手腕關節,P-domain則是手指。現今普遍借用纖維母細胞上經典的肌動蛋白絲逆行跑步機模型(retrograde treadmill model)來說明如何藉由肌動蛋白-肌球蛋白系統,使軸突末梢產生兩種類型的機械力:1)由 T-zone中的肌動蛋白弧(actin arc) NMII驅動的收縮力,和 2)由 P-domain 中的 F-肌動蛋白聚合所驅動的推力。所謂的逆行跑步機指的是原本與NMII結合會讓肌動蛋白絲向後逆行,但當細胞膜上的整合素-貼附蛋白體(Integrin-focal adhesion complex)鉗住肌動蛋白絲時,肌動蛋白絲增加向前聚合的效率,並且原本肌球蛋白向後的拉動肌動蛋白絲的拉力,反而轉換成將固定肌動蛋白絲的支點往前推的推力(類似我們用手指頭撥動滑鼠滾輪的動作)。
不同的物理環境,將生長錐改頭換面。 然而腦是所有體內最柔軟的器官(由於脂質蛋白含量極高),這些細胞骨架當神經軸突與生長錐在極軟的組織物力環境時,能否使用與生長在塑膠培養皿或玻片上相同的邏輯來運作是需要進一步檢視的。於是科學家利用水膠材製造出相似於腦的軟度的培養環境,再次應證Cajal百年前的敘述:無論是在二維或三維的軟環境之內,軸突末梢的T-zone並不像張開的手掌,而是像個握緊的拳頭。那一切就都合理了!在不易產生穩定的貼附力的軟環境下,整個神經元型體由於細胞膜張力增加而更為立體,生長錐頂部T-zone的 肌動蛋白弧也轉換成不受路徑上較無用的貼附訊息干擾的作用模式,反倒成為一個能聚集微管末梢的結實結構(像戴了個有夜視儀的戰技頭盔)。而不斷延長且集中的微管束,自然產生一個向前的推力,就由著變形蟲式的前進,便可機械性地推開擋在它的路徑上的阻礙。這才是Cajal形容的柔軟而靈活的攻城錘。
新生即是再生。近幾十年來,我們對神經系統如何發展的理解獲得令人矚目的進展。深入到分子細節的層面,我們已經了解了神經元是如何誕生的,它們是如何分化的,它們是如何產生軸突和樹突,以及軸突是如何被引導形成突觸與連結的。在這個發育的初始期之後,便進入一段關鍵時期,這段時期內的神經活性具有可塑性,可塑造與穩定神經迴路。當可塑期結束,中樞神經系統才算正式成熟,但也進入無法再生的狀態。而我們正確的理解軸突生長錐在神經細胞發育與成熟的作用機制,將有助我們提供一個如何選擇性地逆轉成熟程序,以重新激活再生過程的切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