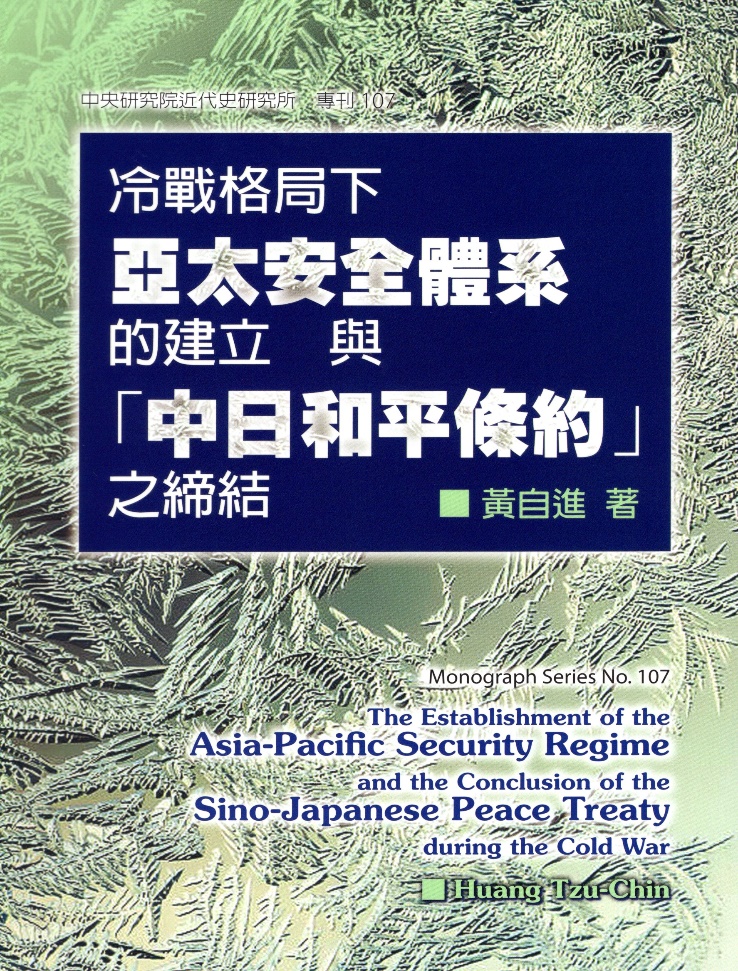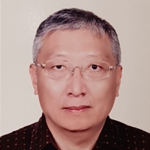
我出身於外省家庭,自幼在臺北長大,循規蹈矩,支持政府,是我成長過程中的基本態度。我於 1980 年赴日本留學,讓我第一次驚覺我的臺灣生活經驗,與周遭人大不相同。當時在我就讀的慶應義塾大學,總計有 200 多位同學來自臺灣,其中純外省籍只有我 1 人,另外 1 位女同學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閩南人。換言之,我是在東京面對一個幾乎全是本省籍的社交圈時,才發覺我在臺北時是生活在族群的藩籬之中。
「不談政治」,是我在日本留學時所秉持的原則,也因而讓我開始得以結交一些本省籍友人,其中包括我的伴侶。聽內人的二舅說,我之所以得以進入他們的家庭,是因我岳母一再保證「我雖是外省人,但絕不是國民黨黨員」。
我的岳父是臺中人,在新竹長大,日語是他的母語,臺語與國語是臺灣光復後,才開始學習。對他而言,讓他覺得與同儕溝通順暢,反而是退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以後;在那邊他所參加同鄉會通用語言是日語,除了沒有語言障礙,成員們相同的成長背景,讓他得以找回童年時代的記憶。
個人的成長過程、留學的經歷、進入本省家庭的歷程,三個不同的階段,也讓我見識到外省族群、本省族群及日治時期皇民化家族的三個臺灣不同面向。而令我感觸最深的是 2000 年總統大選,岳父母乘包機趕回臺灣投票。看到從不參與政黨活動的他們,談起民進黨可望執政時的興奮,也讓我體會到他們的執著和認同的力量。
2000 年後的臺灣雖有幸可邁入政黨輪替的民主時代,但每一次的總統大選,皆會造成意識形態對立、族群撕裂、甚至國家認同的挑戰。近年來我一再思索我國選舉政治上認同的強烈對立,是否肇因於長期以來國人對史實和真相認知視角的歧異?故如何跳脫意識形態和自身認同,也成為我在撰寫「中日和平條約」這個同樣涉及國家認同問題時,得一再調整研究取徑的緣由。
1952 年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顧名思義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之間所簽署的雙邊條約,但事實上,卻是美國為了落實圍堵思維一手主導的產物,其目的在於有效封鎖共產主義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因而它蘊含多重政治意義,尤其以和約的簽訂是否已完成臺灣主權移轉的法律程序,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迄今爭論不休的熱門議題。特別是臺灣主權歸屬,與是否認同中華民國體制的論述,已成一體兩面的共生關係。臺灣主權歸屬的爭議,不僅是學術界歷久不衰的爭辯課題,有時更成為學者個人表達政治立場的一項重要指標。
該和約中雖規範了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等地的一切權利,但沒有明文交代此等權利的移交對象,卻又將臺灣、澎湖的居民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納入中華民國政府管轄。此等將「一切權利」與「管轄權」刻意分割成兩個不同名目的安排方式,確是和平條約中的罕見特例。再則,和約本是為了終結中日兩國的戰爭關係而締結,和約的適用範圍,限定適用於臺灣地區,而不及兩國真正有戰事行為的大陸地區;讓立約的目的,與立約所強調的精神猶如南轅北轍。這些互相扞格的內容規範,竟然可同時納入,自然也是造成日後何以學者對條約可以有完全相反解讀的緣由。
受外交部委託整理「中日和平條約」檔案,開啟了我個人對和平條約研究。初步研究的心得刊登在本院近代史所集刊的〈戰後臺灣主權爭議與中日和平條約〉(2006)一文,該文著重於解析和約的簽訂始末,尤其是聚焦於主權歸屬問題的探索。個人認為主權只是抽象的法律概念,唯有「管轄權」的具體行使,才能彰顯主權的實質內涵。全文亦根據此一研究心得,主張中華民國因得力於此和約的簽訂,而得以從原日本宗主國手中,取得臺灣主權。
個人的研究心得,雖被本院選為該年度的重要研究成果,但也遭眾多不認同此一觀點的學術界同儕質疑。我遂藉本院舉辦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機會,撰寫〈延續與斷裂:再探《中日和平條約》〉(2013)一文回應;冀望藉由「延續」與「斷裂」兩個不同的視野,重新審思主權爭議以及中日和約所蘊含的政治意涵,強調該和約既有結束兩國戰爭狀態到恢復和平的「延續層面」,亦有分割中國主權,僅以現有管轄領土為條約實施範圍的「斷裂層面」。
不過,從質疑臺灣主權歸屬確定論的聲浪仍然不斷的情勢來看,個人的新嘗試並不能改變學術界對中日和約的既有成見。在面對「主權確定論」與「主權未定論」兩大見解壁壘分明的態勢下,我亦意識到,唯有從新的研究取徑出發,才有可能扭轉學術界對中日和約研究各持己見的對峙局面。由是本人進一步提出國內外學術界對中日和約的關注焦點,不應再局限於臺灣主權歸屬是否確定的個別議題,而應從戰後亞太地區冷戰史的脈絡去解讀中日和平條約蘊含的現實意義。尤其是「臺灣主權未定論」何以會成為美國亞太政策之一環?而此一論述又如何成為中日和平條約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政府何以被美國操縱?以及在戰後美國所規劃的亞太政策架構中,中華民國與日本究竟扮演什麼角色。由此思考解讀中日和約時,才能超越國內的統獨意識,為臺灣學術界提供一個大家皆能接受的史實論述,此亦成為個人努力的新方向。
要言之,個人研究取徑的變化,在於將中日和約的研究範疇從原本局限於中華民國及日本政府之間的兩國互動,提升到在美國的亞太安全體系下,兩國與其他同屬反共陣營盟國之間的互動。因此,本研究更與個人原本進行的戰後日本外交史議題得以結合;重新研究戰後美日兩國化敵為友的過程,遂構成本書第二章的主要內容。
共產勢力在遠東地區的崛起,是促使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關鍵,而支撐美日結成同盟關係的理論基礎則是來自於圍堵思維。這是個人研究戰後美日關係的心得,而美國在遠東地區推展圍堵政策過程中,另一重要的決策改變,就是將其在亞太地區結盟的對象,從中國改為日本。探討戰後國民政府的東北接收失利與中共崛起的因果關係,以及美國結盟對象改變的過程,就成為本書第一章詮釋中日和約簽訂始末時代背景的主旋律。至於戰後的臺灣為何因韓戰的爆發而被納入美國的亞太安全體系,則是個人研究圍堵思維的另一研究成果,亦改寫為本書的第三章。
將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彙整成理解戰後冷戰架構下亞太安全體系的建構過程,是本書的論述主軸。本書意欲開展的新視野,即是將中日和約置於冷戰發展的脈絡中重新定位。當時的美國政府為了因應現實需要,既要讓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立足,又不能讓日本與中共有相善的機會。於是美國在籌劃和平條約時,刻意將眾多引發多重爭議的臺灣主權未定議題、限定和約適用範圍,以及法理代表中國等名與實並不一致的條文,拼湊在一起。由此一來,和約簽訂後的美國仍可主張「臺灣主權未定論」,為今後隨時介入臺海紛爭預留餘地;同時又安排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法統政府,保留其聯合國的席位,以便讓和約能夠充分達到圍堵中共的效益。
藉由《冷戰格局下亞太安全體系的建立與「中日和平條約」之締結》的出版,冀望能將國人對主權歸屬的專注,轉移到中日和約對臺灣所具的現實意義。期許國人能對臺灣進入國際社會的過程、臺灣所能擁有的國際空間及所受的制約,有更清晰的掌握後,更願在現有的基礎上,為今後的臺灣締造更寬廣的國際空間,此不但是個人的心願,亦是推動本書能順利完稿的動力。
相關網址: http:/www.mh.sinica.edu.tw/monographs.aspx